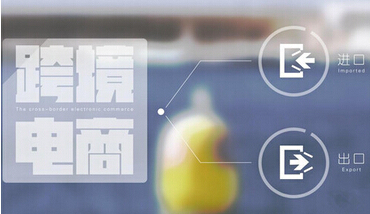“那一天我二十一歲,在我一生的黃金時(shí)代,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愛,想吃,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
后來我才知道,生活就是個(gè)緩慢受錘的過程,人一天天老下去,奢望也一天天消逝,最后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。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(shí)沒有預(yù)見到這一點(diǎn)。
我覺得自己會(huì)永遠(yuǎn)生猛下去,什么也錘不了我。”
最初讀到這段話的時(shí)候,我也剛剛20出頭,還能肆無忌憚地享受大學(xué)時(shí)光,對(duì)前途多的是幻想與憧憬。
這段話看過即忘,對(duì)我并沒構(gòu)成任何心靈的沖擊。
可是現(xiàn)在,30歲已在向我遙遙招手,結(jié)婚、生子、買房、買車、事業(yè)、健康、責(zé)任 .......種種世俗的壓力好像就站在那里等著我,它說,它們說:
“走快點(diǎn)呀,該著急了,你已不是少年人了。”
恍惚間,我回頭去望,那段無憂無慮的少年時(shí)光,已依稀如夢(mèng)、仿若隔世。
年少不識(shí)書中意,讀懂已不再少年。
柳永的一首《少年游·長安古道馬遲遲》,寫盡的原是多少成年人的悵惘、凄涼、不舍與苦澀。
長安古道馬遲遲,
高柳亂蟬嘶。
夕陽鳥外,秋風(fēng)原上,
目斷四天垂。
歸云一去無蹤跡,
何處是前期?
狎興生疏,酒徒蕭索,
不似少年時(shí)。
寫下這首詞的時(shí)候,柳永已不再年少。
長安古道上,他騎著馬兒,緩緩前行。秋蟬在高高的柳樹上鳴叫,叫得人的心上也一片紛亂哀凄。
夕陽在飛鳥外的遠(yuǎn)方漸漸沉落,曠野荒原上秋風(fēng)習(xí)習(xí)。
他極目四望,渺無人煙,唯有空蕩蕩的天空如幕帳般向下四垂。
那些過往的時(shí)光如飄逝的云彩般,一去無跡。舊日許下的約定與期望,又該向何處尋覓?
從前那些尋歡作樂的興致,如今早已淡漠了;那些一起喝酒的朋友,也零落無蹤了。我也不再是那個(gè)狂放不羈的少年人。
柳永的一生中,寫下過許多首《少年游》,甚至有人說,這個(gè)詞牌名便是由柳永所創(chuàng)。
“少年”二字,是單單聽著,都會(huì)讓人感到心頭澎湃著的意氣風(fēng)發(fā)。
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少年》里寫下的:
“少年就是少年,他們看春風(fēng)不喜,看夏蟬不煩,看秋風(fēng)不悲,看冬雪不嘆,看滿身富貴懶察覺,看不公不允敢面對(duì),只因他們是少年。”
可柳永筆下的《少年游》,卻總是蕭條冷落。
一如這首《少年游·參差煙樹灞陵橋》,“參差煙樹灞陵橋。風(fēng)物盡前朝。衰楊古柳,幾經(jīng)攀折,憔悴楚宮腰。”
一如這首《少年游·十之八·林鐘商》,“一生贏得是凄涼。追前事、暗心傷。好天良夜,深屏香被,爭(zhēng)忍便相忘。”
一如這首《少年游·長安古道馬遲遲》,“狎興生疏,酒徒蕭索,不似少年時(shí)。”
曾幾何時(shí),柳永也曾是一個(gè)狂妄至極的少年人 。
他少有才名,天性浪漫,一首《望海潮》令他名滿天下。
誰知考場(chǎng)失利,他滿腔憤懣與桀驁,化作一首《鶴沖天》:
未遂風(fēng)云便,爭(zhēng)不恣狂蕩,何須論得喪?
才子詞人,自是白衣卿相。
功名利祿算什么?仕宦大夫算什么?做一個(gè)風(fēng)流才子為歌姬譜寫辭章,即使身著白衣,也不亞于公卿將相。
那時(shí)的他自矜自傲,也是真的無所畏懼。
前途尚遠(yuǎn),春光正好,有什么好去計(jì)較在意的。且去飲酒,且去高歌,且去揮霍。
反正我們尚年少,日子還長著呢。
可是一轉(zhuǎn)眼,只是一轉(zhuǎn)眼,光陰就成了故事,歲月也成了風(fēng)景。
昔日的青春柔嫩,已成今日的滿臉風(fēng)霜。
人生何其匆匆啊!
柳永大半生的時(shí)光,都在科考場(chǎng)上、煙花場(chǎng)上蹉跎而過。
四次科考,四次不中;待到第五次終于高中,他已然到了知天命的年紀(jì)。
喜悅之余,更多的還是悵惘吧。
一如小的時(shí)候,想看某部電視劇卻不被應(yīng)允,只得“含恨”埋首書堆。待到長大,終于有時(shí)間有能力去看的時(shí)候,已不再有看的心情了。
“狎興生疏,酒徒蕭索,不似少年時(shí)”,便該是這般的心情吧。
我這才讀懂,最愛說“少年”二字的,往往并不是正青春的少年人,而是如你、如我一般,已不再年少的成年人。
“少年不識(shí)愁滋味,愛上層樓,愛上層樓,為賦新詞強(qiáng)說愁。”(辛棄疾《丑奴兒·書博山道中壁》)
“如今卻憶江南樂,當(dāng)時(shí)年少春衫薄。”(韋莊《菩薩蠻》)
“欲買桂花同載酒,終不似,少年游。”(劉過《唐多令》)
也許30歲,也許40歲,也許50歲,也許60歲......讀著詩篇也是好的,無非是因著自己已回不去了啊!
“少年不識(shí)愁滋味”,原是與“人生若只如初見”一般的,逼人的蒼涼冷意。
只因說出這一句話時(shí),人生已再回不到初見的時(shí)候,而我們也再不是“不識(shí)愁滋味”的少年人。
“我長大了,我是一個(gè)成年人了”,生活在一遍遍地提醒著我、我們。
我們已不再無所畏懼,只因有了軟肋;但我們也可以無所畏懼,只因那軟肋也是鎧甲。
我們已不再天真純粹,只因已歷經(jīng)過風(fēng)霜;但我們也可以天真純粹,只因那些風(fēng)霜讓我們更通透澄明。